2022 年 4 月,距离 1·20 北京朝阳医院伤医事件已过去两年多的时间,作为该事件受害者之一的眼科医生陶勇,左手断掉的神经仍未长好。
那是一只做过 1 万 5 千多台眼科手术的手,原本灵巧而稳定,如今却无法伸直,动作受限,再也无法操作高精度的眼科手术。
而陶勇也已经接纳了这一切。从鬼门关逃出后的他,对自我的生命历程、个体与周遭的关系、治病与救人的方向也有了更多的思考。
思考使陶勇进入到更宽广的生命之圆里,一幅世界地图似乎就在他眼前徐徐打开。在那一片明亮与广阔里,也有缺片和留白。
于是,他好奇身边那些充满可能性的碎片,好奇它们将如何填满地图上缺失的一角,而伴随这种好奇的,是一种唯有在纯真者身上才有的相信 ——“无论是什么样的碎片,我都相信,它会让我面前的这幅世界地图更完整”,正如他从来不愿把别人想得特别坏,正如他在直面黑暗后仍旧选择相信这个人间。
而这种对人对事的态度,并不是陶勇在受伤后才有的,这不是一种结果,而是一种本质状态。
再有不到一个月,他就四十二岁了,作为一名医生,他看过太多无奈的世情,自身也经历过不幸的际遇,但几乎所有接触过他的人都会感觉到,在他身上,有种“少年气息”从未离开过,那是对世界的好奇,对光明的热爱,以及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幽默与可爱。
尽管不能亲自做手术了,这两年多来,他依旧会出门诊、指导手术、从事科研。同时,他也做了许多新的尝试,比如投身公益、参加演讲、写书等。除了眼科专著《眼内液检测的临床应用》,他还陆续出版了《目光》《自造》等面向大众的作品。
随着生命的成熟,陶勇还有一种感觉 ——那些过去看似无用的碎片,正在悄悄连点成线,它们的存在,的确让他眼前的地图愈加完整。
时光倒流回八十年代,彼时,由于母亲在新华书店工作,书店就成了陶勇常去的地方,在那片书籍的海洋里,父母从不限定陶勇要读什么书,于是,那个小小少年不管什么书都翻一翻,武侠小说、经典名著 …… 哪本好看就读哪本。
几十年后,陶勇回忆往事时,觉得那些没有目的、看似无用的事情,已在不知不觉间对他产生了作用。他发现,他的内核其实是一个务虚的内核,是一个形而上的内核,也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内核,而这种内核,就是在广泛阅读和非功利性阅读的过程中塑造的。
一切正如威廉 · 吉布森在《全息玫瑰碎片》里写的,每一个碎片都从不同角度揭示着玫瑰的模样。那些出现在生命中的人和事,都让陶勇对人生有了更多的认识。
在这个枝枝蔓蔓绵延依旧的春日,ZAKER 新闻对陶勇进行了专访,我们捡拾碎片,聊聊碎片。
陶勇:我自己一直是喜欢写点东西、喜欢总结的,这两年,我也有了很多感触。我去了十多所大学,包括清华、北大等,接触了很多同学,这些都是在千军万马中通过了独木桥的天之骄子,但他们对人生有很多迷茫,觉得人生找不到方向。
我作为一个医生,治疗眼病是我的使命,除此之外,帮助这些青年人更好地找到自己的人生意义和方向,我觉得我也有一种责任。我的天性让我愿意去分享自己的经验 —— 就是在医学这样一个看似很枯燥无聊、甚至有风险的一个行业里,如何能一直保持很大的乐趣、坚持到今天。我希望透过医学窥镜,把一些想法分享给大家。
陶勇:都是解决问题?做手术其实就是,发现了哪儿有异常的组织,我们要把它切除,然后写书也是一样,因为你不可能完全是无病呻吟,而是当你发现了有这样的一些问题,然后你愿意给出你的一个处方,你才会去写作。
陶勇:我觉得这两个,哪个也不能取代另一个,它们是并存的,就像快餐和美食,我们都需要。尽管快餐可能不如美食那么营养丰富,但有总是比没有强,而美食则能满足一些有更深层需求的人的需要,相对而言可能更小众。
浅阅读和深阅读不存在矛盾。很多读者一开始可能是浅阅读,但是读着读着,当他们读到了一本两本好书,当他们发现这些书跟他的生活能够产生一个关联和共鸣的时候,可能他就会选择垂类里头的书,进行深阅读了。
陶勇:如果按照世俗的观点,可能几乎所有的书都是没有用的。作为一个动物的人,满足了生理需求、补充能量就可以了,不需要读书,所以原始人类就不需要书。
“用”本身来说就是意义,我认为这是个动词,它并不是在当下就能够显现出来,很可能需要一段时间,你才知道它有用还是没用。
陶勇:我觉得人生可能分为两个阶段。一个阶段是模仿,别人教你,比如你想学做菜,就读一些关于怎么做菜的工具书,然后就模仿。
但是还有一个阶段是超越。在这个阶段,可能不一定能找到答案,有些事情可能需要你自己创新,用独立思考的能力,自己去辨明方向,去找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。在这个过程中,其实读“无用之书”是很有帮助的,因为它突破了你思想的边界,可以让你插上想象的翅膀。
陶勇:这倒不会,因为人要尊重规律。你可以对年轻人的世界有好奇,想要了解更多,但是你没有必要非得把自己按在那个位置上。我没有很焦虑,我就觉得自己会很开心,因为一直对生活有好奇。
这种感觉就像,一幅世界地图摆在我的眼前,但这个世界地图不完整,所以我会很好奇,不知道身边的这些年轻人,不知道我看过的这些书,不知道我经历过的这些事儿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碎片。但无论是什么样的碎片,我都相信它会让我的世界地图变得更完整,所以我不会焦虑,而是觉得很开心。
陶勇:加缪说过,有的人 40 岁时死于自己 20 岁时向自己心脏开出的那颗子弹。所以,如果你自己觉得,我已经落伍了,我已经过时了,这会不自觉地给你上了一道精神枷锁,就会限制你的进步。
陶勇: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,太极图是很典型的,有阴有阳,阴里边包着阳,阳里边又包着阴。在你刚才说的“不确定性”面前,我们的应对方式无非两种,一是用冷漠包住自己炽热的内心,二是用一个开放探索的内心去包住那个冰冷的寒冬。
对于我来说,其实我并不想去改变每个人的习惯性做法,我并不想去说教、同化别人。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经历的事情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苦,你只是单纯地说 —— 你就应该振作起来、你就应该怎样,我觉得这是脱离现实的说教,没有太多意义。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沉浸在那种生活的陷阱之中,我们没有经历过人家生活中的一些苦恼。
陶勇:我觉得,我们可以做到的是形成一个环境,就是当冷漠的人多了,它就会变成一个寒冬。而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变成一片绿叶的时候,春天不知不觉就会来到。
我们能做的事,就是告诉大家,你可以用阳包住阴,告诉大家,我们可以去形成一片春天,形成一个环境,用一个温暖的环境去抵御凛冽的寒风。
陶勇:好的。“光盲计划”涉及到两个方面 —— 科学和人文。一方面,我们要用科技的手段,如干细胞技术、眼内液检测技术、基因治疗技术以及脑机接口技术等,不断利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手段,让更多人避免因为误诊、误治而失明,让更多的盲人有恢复光明的可能,将光明引入眼中;另外一方面,针对那些已经失明和低视力的人群,我们采用心理关爱、生活重建、职业培训、再就业指导等措施,让他们仍然可能寻找到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,失去光明,但不失去希望,用人文将希望引入心中。
这个计划,是我们一辈子要去做的事,这件事情一方面要去科研开发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,另外一方面也要借助科普手段及公益方式,将人文和科学两方面都做好。
陶勇:当下最主要的是两个项目,一个是巨细胞病毒视网膜炎的人工智能筛查项目,一个是盲校录音棚项目。这两个项目我们已经启动了,一个是在北京市儿童医院有落地,还有一个是在北京市盲人学校有落地。我们接下来会花很多的时间把这两个项目先打造起来,同时一点一点地复制、扩大到全国的其他地区。
陶勇:这是一本关于眼健康知识介绍的科普漫画书。之所以写这本书有两方面原因,一方面,我本人是一名眼科医生,我知道近视在现在已成为危害青少年健康的一个普遍的眼病,国家也是高度重视,但这个眼病也有很多误区,大众其实需要了解。
另一方面,自己作为孩子的爸爸,也是希望中国家庭的爸爸妈妈们多多关注孩子的视力情况,希望孩子们不会因为学习任务重而影响了视力。
陶勇:首先是内容策划,例如要科普哪些疾病,然后是把关、反复斟酌,思考怎么能让孩子喜欢。这里头最大的挑战,我觉得其实就是怎么用孩子喜欢的语言把这些科普知识呈现出来。
陶勇:因为我女儿的名字叫陶陶,两个字都是陶,当时起这个名字也是因为乐陶陶嘛,希望她很开心快乐。陶小淘这个名字就是从我女儿的名字衍生来的,同时,也希望用这样一个带有喜感的名字,带给孩子们亲切的感觉。
陶勇:没错,我们全家都很重视孩子的视力。作为眼科医生,我自己是知道的,近视问题,任其发展下去会成为高度近视,眼底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病理性的损害。另外,近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是致盲性眼病,它的危害还是很大的,近视的人群发生视网膜脱离的概率要比非近视的人群高 40 倍。
另外,我觉得,孩子的成绩是一时的,但孩子的视力是一辈子的。所以,我希望我的孩子不要以眼健康为代价来换取成绩,那是不划算的。
陶勇:未来还会出一本书,叫《壮壮寻医记》,我有一位盲人患者小朋友叫薇薇,也喜欢写作,所以我们一起创作了这本小说,但是很短,是只有三四万字的一本小小说,讲述的是来自农村的壮壮在患上了眼疾之后,如何不放弃自己、孤身一人去城里寻医的故事。
陶勇:书籍本身是一盏明灯,我们需要用阅读这种方式开灯,然后你会发现,原本黑白的世界一片光明。
采访、撰稿 / 黄靖
设计 / 陆盛华 卢键昌
视频 / 陈泽欣 李永煜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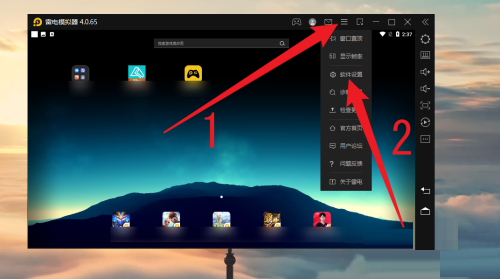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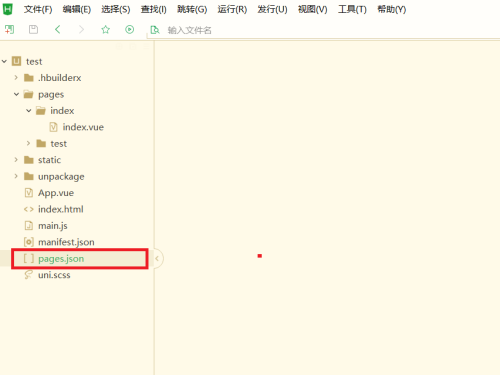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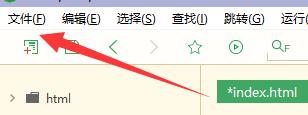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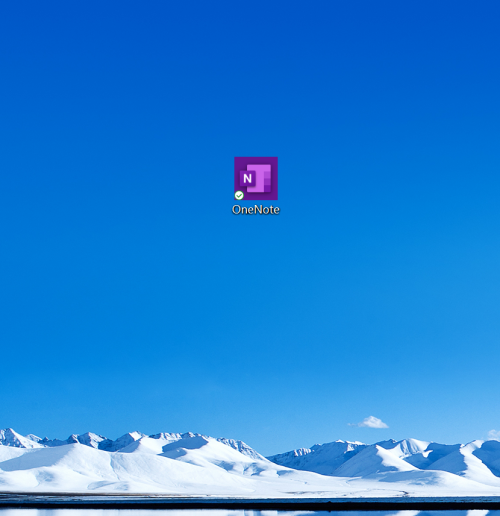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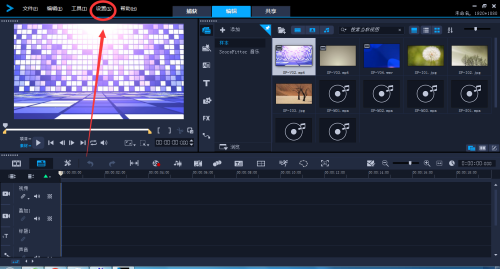



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
营业执照公示信息